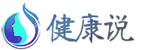作为一个才能平庸、“在各个方面都很弱的人”,勃列日涅夫在他担任苏共总书记的十余年中,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印象,或许莫过于“勃列日涅夫之吻”。
接吻虽是俄罗斯人久已有之的礼节传统,但在勃氏上台之前,这种传统并没有正式进入政治生活,只是偶有发生。譬如: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米高扬至其家中,向赫氏传达关于其待遇问题的决定,告别时,“赫鲁晓夫把他送出了门外,当时并无接吻的习惯,但两人除紧紧地拥抱外还是情不自禁地把嘴亲在了一起。”
因个人喜好,“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政治局委员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见时,男人互相接吻的礼节。”在勃氏看来,这或许是他展现个人外交魅力的独门法宝,但被其接吻的各国政要,鲜有情愿与开心者。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在其回忆录中,曾如此讲述他被勃氏多次强吻的经历:
1979年10月4日,勃列日涅夫(左)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右)在庆祝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庆典上激烈拥吻“勃列日涅夫以俄罗斯典型的、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男子接吻习惯而闻名。……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为本人公开活动的一个突出部分,来加以运用。比如,他1963年12月来布拉迪斯拉发,我到机场欢迎他时,他拥抱和吻我就没有来由。我们在这以前从未见过面。五年之后,又是在公开场合,在糟得多的情况下,他又试图这么做。”
有了之前惨痛的“被强吻”教训,1968年8月,勃氏再度造访时,杜布切克已有了应对之策:
“我在布拉迪斯拉发机场等侯时,对他已有准备。我左手拿着一大束鲜花,决定用它作挡箭牌,使勃列日涅夫同我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事情正如我所料。他立即来找我,但我成功地用花把他挡开,他抓住我拿着花的手,使劲把它举到空中。摄影记者就这样给我们拍照。不过,照片未披露此前的小小斗争。”
俄裔美国石油巨头阿莫德·哈默,也对“勃列日涅夫之吻”相当反感。他在自传中写道:
“随着我们对勃列日涅夫结识的加深,我们也不得不习惯于他在欢迎特殊朋友时那种特殊的方式。我曾经被数以千计的俄国男人吻过,尽管这样的经历还是没有为好,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吻我的面颊。而勃列日涅夫则不同,他表示特殊尊敬的方式是使劲地亲吻你的嘴唇。
1979年,勃列日涅夫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谢拉夫热吻最厌恶“勃列日涅夫之吻”者,要数苏共政治局委员们
对“勃列日涅夫之吻”最深恶痛绝者,莫过于勃氏下面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毕竟,他国政要毕生至多也不过被勃氏“强吻”数次而已,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却不得不“上行下效”,时刻致力于将“勃列日涅夫之吻”发扬光大。继勃氏之后的两任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相当痛恨这种“接吻”:
“安德罗波夫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在一次同患病的泽登巴尔(笔者注:蒙古人民革命党书记)接吻后患了重感冒。”契尔年科早就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极容易感冒”,但为竞逐总书记宝座一直竭力掩饰,所以,“这种接吻对于契尔年科,简直是致命的。”
政治局委员们在公开活动中,积极效仿勃氏到处接吻,私下里则常拿“勃列日涅夫之吻”取笑。如1979年6月,勃氏与美国总统卡特会晤签署削减武器条约,出席签字仪式的葛罗米柯,就与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讨论“他们会不会热烈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