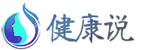徐枣枣坦承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她希望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大到能让政策制定者看到。(受访者供图)
- 1我看到她(徐静蕾)接受媒体采访的自述,才理解了冻卵对于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 2我并不觉得,几年前不想生育,后来改变想法了就是后悔。我更倾向于将冻卵看成买一份“保险”。
- 3作为一个从小在父母相对来说打压式的、比较严格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能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为自己而活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 4冻卵是想保存我的生育能力,跟我有没有伴侣,或者和伴侣的关系怎么样都无关。
开庭前,徐枣枣特意把头发剪得更短了,染了金色。她说想展现自己精干、有力量的一面。
她是全国首例冻卵案当事人。一年多前,徐枣枣刚满三十岁,获得一次工作晋升,既面临机会,也承受着压力。身体发生的微妙变化让她陷入焦虑,她开始寻求一个出口:冻卵。
在中国的政策规定里,冻卵这项生殖技术尚不能提供给单身女性。两次就医却被催生之后,徐枣枣选择了运用法律手段,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告上法庭。但在立案之初,她又吃了数次闭门羹。她也曾陷入纠结:单身女性有没有保障自己生育权利的权利?
2019年12月23日,冻卵案第一次开庭,双方陈述之后,以休庭告一段落。次日,徐枣枣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正常采访时,坦承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她明白很难胜诉,但希望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大到能让政策制定者看到。
医院方有说苦衷
南方周末:第一次开庭是什么场景?
徐枣枣:开庭后,我们陈述了基本事实,表达了冻卵的诉求。法官可能也考虑到此案受媒体关注度高,表示要对冻卵这一专业领域做些研究,中午就宣布休庭了。
南方周末:医院的代表在庭上如何回应?
徐枣枣:医院方有说苦衷。医生谈到,现在全国任何生殖中心或者相关人工生殖技术辅助科,按照政策都不可能给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这话其实也传递了很多信息。相关主管部门对医疗单位的约束性规范就是如此。是很无奈的。
南方周末:对方律师怎么说?
徐枣枣:除了政策,对方律师也把手术风险拿出来讨论了。比如,打促排卵针的时候有一定的概率会导致对卵巢有过度的刺激;取卵过程中,用针头做阴道穿刺的时候,是要从女性的阴道口插入的。
南方周末:担心破坏处女膜?
徐枣枣:对方律师的话语间,给我感觉医院有道德责任维护单身女性的处女膜完整。穿刺过程,还有可能造成内脏的一些过度挤压。
另一方面,冷冻卵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卵子活性可能降低,复苏率受限制。我之前了解的复苏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如果是冻胚胎的话会高一些。
南方周末:那你此前了解过这些风险吗?
徐枣枣:基本都了解过。其实他说的这些风险,不能否认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每个手术都有风险。
三十岁女性的现实焦虑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了解冻卵,是在何时?
徐枣枣:四五年前,徐静蕾冻卵的新闻出来了之后。我看到她接受媒体采访的自述,才理解了冻卵对于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徐静蕾)用的词是“后悔药”。现在可能并不想生育或者没有这个生孩子的计划,以后也许会有。
南方周末:你也想为自己准备一粒“后悔药”?
徐枣枣:“后悔药”这个词听起来相对负面。我并不觉得,几年前不想生育,后来改变想法了就是后悔。我更倾向于将冻卵看成买一份“保险”。
现在(考虑)是否生育对我来说是个烦恼,但如果冻卵了,可以推迟几年再做这个决定。人应该随时都有就现阶段的状况、想法,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
南方周末:所以你是何时开始下决心去做冻卵的?
徐枣枣:去年(2018年)冬天。
南方周末:徐静蕾冻卵也是好几年前了,有什么契机让你去年这个时点下定决心呢?
徐枣枣:还在于我去年满三十岁了。
而且2018年,我工作上得到晋升。我是从事新媒体行业的,去年开始承担一些管理岗工作,这让我觉得工作生活都处于上升阶段。以后生活在什么城市,要不要再去继续读书深造,都未可知。
南方周末:晋升也代表着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增大?
徐枣枣:新媒体行业可能看起来现在还比较火,但随着国家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加强),我发现有很多问题。
这个行业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从职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我需要找一些出口,比如专业技能和人脉、资源,做什么相关领域的工作能更好地去继续增加我的不可替代性,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些都是让我想冻卵的因素。我意识到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处理它们。
与此同时,我也面临迈入三十岁的门槛。我发现和二十岁时相比,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方周末:能具体举例吗?
徐枣枣:比如说新陈代谢明显变慢了。二十来岁的时候喝酒还可以喝一些,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如果头一天晚上去喝酒,很累的话,第二天可能一天状态都很难回来。
比如说原来我一直觉得怎么吃喝,身体不会太发胖,但是快三十,我开始发现如果不健身,不保持规律的运动,就可能发福。还有关于外貌的焦虑,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皱纹,是不是皮肤变差……
这些细小的焦虑填满了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让自己能够真切感觉得到。
按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活着是需要学习的
南方周末:这种焦虑之下,你的生育观是怎样的?
徐枣枣:我大概在25岁时,坚定了不婚不育的想法。育儿、和小孩沟通是很需要耐心的事情。我也不觉得这是我这个年龄段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可能我更想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生活空间,不需要把过多时间和注意力投放到其他人的身上。
南方周末:这种想法的产生和你的原生家庭有关吗?你是独生子女吗?
徐枣枣:我是独生子女。作为一个从小在父母相对来说打压式的、比较严格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能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为自己而活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小时候被教育得比较没有自信。所以成年以后,尤其是开始有社会交往,在职业方面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就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专注在自己身上,慢慢恢复和建立自己稳定的社会性。
被告知需要照顾别人的感受,给别人做情绪劳动,很多时候需要牺牲自己的想法去听从别人,我得到这类信息已经太多了。反倒是按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活着是需要学习的。
南方周末:但当时你是25岁,到了30岁,不婚不育的想法有改变吗?是否因为有所改变才想冻卵?
徐枣枣: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受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现在也没法评估我五年后会怎么想。目前为止,我也不觉得以后一定要生育,但想留下健康的卵子以备不时之需。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
徐枣枣:我目前是在一段恋爱关系中,这段关系的开始晚于我产生冻卵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和另一半讨论过这事吗?
徐枣枣:有,我和他开始比较熟悉的时候,就说过我在准备冻卵,并且遇到一些困难。
他现在还是比较支持的。我会直接说,这个计划是为我多年以后的选择做准备。早在我们关系开始前,我就决定要做这件事了。哪怕你反对,我也会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南方周末:他的存在有没有可能改变你的诉求?
徐枣枣:冻卵是想保存我的生育能力,跟我有没有伴侣,或者和伴侣的关系怎么样都无关。普通人眼中,似乎女人的身体、女人的生育还是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家人,如父母、男朋友、老公、儿子约束。
单身女性在生殖科甚至无法挂号
南方周末:第一次去医院是何时?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妇产医院?
徐枣枣:此前联系很多家医院都被拒了。单身女性在他们医院的生殖科网上都无法挂号,打了电话咨询才知道,生殖科只接受现场挂号,并且现场挂号的时候,就得有身份证明,证明你已婚。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连医院门都进不去。妇产医院挂号时没有类似规定。
我第一次去妇产医院就诊是2018年11月14日。
南方周末:这次面诊你和医生谈了些什么?
徐枣枣:我开门见山表示想要冻卵。医生询问了我身体的基本情况之后,很随口问了一句:“对了,你是已婚吧。”
我说不是,又表达了冻卵的强烈诉求。医生说国家有相关规定不能给单身女性冻卵,但她并没有花重点的时间和精力在向我解释这个规定。也没有对冻卵这项技术做专业的说明。
南方周末:医生重点说了什么?
徐枣枣:她跟我说话的语气,好像我是一个小姑娘,她是一个过来人,经验比较丰富的知心大姐姐。她就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紧把结婚证领到,然后把孩子生了,事业可以以后再做。
她还举了一些例子,大龄产妇会感觉自己带孩子体力不济,产后恢复的时间也比较长。后来还是说可以给我做一系列健康方面的检查,比如说评估卵巢状态,我就去做检查了。
一个月后,检查出来我去复诊,医生说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良好,很适合备孕生育或者冻卵。
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我也不想那么快被医生打发走。我咨询医生国内冻卵技术是否发展成熟,她也给我比较肯定的回答。这家医院还有给一名癌症女性冻卵成功的先例。
医生表示理解我的诉求,但是不得不面对目前的政策现状。
我听下来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指的就是对单身女性比较友好的相关政策或规范的出台。
南方周末:那你考虑过出国冻卵吗?
徐枣枣:我有朋友在美国读书,顺便在那边冻卵。她说就是非常随意、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价格有高有低,花费比国内过去冻卵便宜很多。
我咨询过中介公司,去泰国的报价是十万左右,美国的话可能是二十万上下,这不仅是手术,还包括食宿、陪同翻译等。另外还有每年的保管费。
南方周末:和成功冻卵的朋友,有什么交流?
徐枣枣:她们知道我要在国内冻卵的时候,就是说挺不容易的。她们觉得单身女性的诉求应该被看见。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冻卵(如果要出国),似乎成了某种“特权”。
数次立案遭拒
南方周末:被医院拒绝以后,怎么会想要通过诉讼这个方式解决?
徐枣枣:最开始也是挺纠结的,因为两次就医经历都让我比较挫败。
诉讼会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律师也和我说,要先评估一下自己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只是案件本身的输和赢,那胜诉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但如果是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影响,对社会文化中一些刻板印象,甚至歧视,带来一些冲击和改变。甚至是让政策制定者能看到单身女性的诉求。冲着这些,这个事情也能做的。
南方周末:所以通过造势来推动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开放是你做这件事的目的?
徐枣枣:对于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障,其实是一个时间问题。
既然是早晚,如果我通过一点努力,能让卵子在黄金时期得到保存,对我自己来说肯定是很好的,这是我一个人的需求,对其他女性来说也是好事。
起诉有一定代价和成本。但冻卵确实是处理我现阶段现实焦虑的一个出口,至少目前的律师费还没有出国冻卵需要的费用那么多。
第一次立案失败了。是今年(2019年)3月底,我和律师一起去了两三回(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最开始用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这个案由,法官说这个案由不成立。因为手术尚未发生,医患关系是双方选择的结果。
南方周末:去两三次都没有立案,对你的心理有没有影响?
徐枣枣:肯定会有的,我一开始去,法官也是劝退。劝退的主要理由倒不是关于案由。他花比较多时间跟我说,他们不得不依据现有法律和法规来。我们国家的生育文化相对于西方国家还比较保守,单身生育存在一定的伦理争议。
南方周末:你动摇过吗?
徐枣枣:单身女性在有生育意愿或者保存生育(权利)这件事上真的这么理亏吗?有段时间我有这样的疑惑。
后来偶然一次,我去听了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向贤的讲座。王向贤一直在研究性别社会学,她用一个非常女性性别视角的角度去谈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变迁和社会影响。哪个时代节点上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年代的女性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像我以前听到那些大国强国人口论——就是什么现在出生率很低,对国家来说很危险,要想一些办法让女性生孩子等等。这些听不出对女性个体生育意愿的尊重,你听了会非常难受。
那场讲座提供了另一种非常平等的视角。我听完以后很受鼓舞,重新变得振奋。
南方周末:你和父母交流过冻卵这件事吗?
徐枣枣:有讨论。一两年之前,我母亲给我转发了一个关于单身生育的地方性新闻,并且问我说你想不想自己生个小孩。我觉得挺意外的,没想到他们会主动跟我来聊这个。虽然我那时也暂时完全不考虑生孩子。
南方周末:他们知道你坚定不婚不育吗?
徐枣枣:我从25岁开始就跟他们讲我是不婚主义者。我妈一开始也逼过婚,帮我找相亲对象。失败之后,可能又想直接催生。
南方周末:他们现在知道你正在争取这个事吗?
徐枣枣:关于这次起诉的事,没有详细正面跟他们沟通过。我之前跟母亲谈到过想在国内冻卵,但有一些困难,我还在想办法。她只是问了我这项技术是怎样的。
(应受访者要求,徐枣枣系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戴画雨